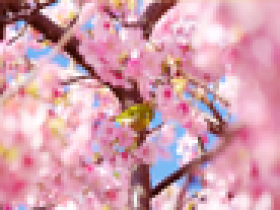- A+
河堤上人很多,三五成群。我的村庄被一畦挨一畦的水田包围着。
又是一年的农忙季节,河流奔涌,绿柳成荫,秧苗也要急着扎根到更广阔的水域里去。三五成群的里面有我,我是被雇佣的人,我成了一名全副武装的插秧工。
其实,我被雇佣完全被动。
有人想在一天内完工,委托大姐凑齐六人。在旺季,人手常常紧俏,因为缺少一人,大姐犯了愁。一向懂得用人的她偷偷跟雇主讲,我家有一高手,心里出巧,干啥啥好,只是——只是不能轻易出山。你瞧,二十来年过去了,一次都没有。出山一词引得雇主眼睛亮晶晶的,好像捡到了宝。她家辈份小,人那么老还要唤我小姑。她笑眯眯找到我,话没说上两句,小姑叫了八个。她的目的只有一个,请我出山,明天帮忙伸把手。开始我不想去,我认为自己当雇工还不够资格。但转念一想自己还算有点儿功底,从七岁开始学插秧,到雇工这一年泥水里摸爬滚打整整十多年,临近上大学要远走他乡了,无所事事的我去也无妨,何况还能收到一笔佣金。大姐推荐我正合适,看雇主诚恳,我同意。
下水后才知道,插秧工的速度和质量都要求一流。我没有传说中那么合格,速度倒是赶得上,但明显吃力。不起身,一直猫腰后退,我总是最后一个靠岸。没等长舒一口气呢,他们一个挨一个下饺子一样蹦蹬一下踩进田里,猫腰搂秧,鸡啄米一般继续;质量一定要过关的,雇主走来走去,眼睛瞄着我们的手和脚。飘秧不行,有沙沙而来的五月风不停地检验,行距大了不可,小了也不合适,直接影响着秋天的收成。雇主不打车会相车,会适时巧妙地给出建设性意见。对经常下场子的人而言,这四脚抓地晾晒屁股的活儿早已轻车熟路。他们一边嘻哈说笑一边“啄米”,两不耽误。而我顾不上多说话,必须保持沉默,一说话就分神,一分神就误工,一旦误工,孤单单形影相吊不说,干啥啥好一说还要穿帮。
远远地看,插秧是一个退步的过程。布袋和尚说的好: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诗中有引申义,凡夫不能觉悟的原因就是不肯“退步”,只知道“向前”。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外境上,总是到外境上去攀缘妄想,而对内心所起的种种错误心念从来不去观察。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肯“低头”、肯“退步”,就一定能渐渐了悟诸法的真相,所以诗中说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。对我而言,插秧就是历练,是内心的审视,是向前。
最难打发的是下午时光。热和累向来是孪生姐妹,总是一起来。我偷偷告诉大姐,我要顶不住了,头昏眼花,想就地躺一会儿。大姐一笑,说坚持,你又不是水鸟,躺在水里的感觉不好受。我们去北京插秧,一猫腰就是一个半月,几千块钱说来就来,腰包都鼓鼓的。难道你忘啦,你的花衬衫,你的曲奇饼干……
我忘不了,哪能忘呢?那时候大姐一走就是几十天,同行的人多,梯子搭下来,行李卷和人排成一条线一起上车,敞开的大篷车里满是梳小辫子的脑袋瓜。听说她们去北京郊区,住八人大火炕,说是火炕,没有人为她们烧火。有人肠胃不好,有人妇科有炎症,赶上阴雨绵绵的日子,实在挨不下去了,她们晚上轮流烧火暖炕。办法总是大于困难。在异乡,能用温火慰藉一颗颗奔波流浪的心足矣。
比起大姐一行人,我这一天的插秧算得了什么?苦和累就像天边的余晖,眨眨眼就下去了。
吃晚饭时,大姐试探着说,明天还有活,要不然,再去一天吧。我说好。大姐很满意,估计她想培养我,把我培养成像她一样能干的人。我年轻,想法简单,下雨天打孩子——闲着也是闲着。没想到,随着时间的推移,事情急转弯,并没有沿着预计的轨道进行,那一次插秧也就成了我今生唯一的一次经历。
事情是这样的,雇主来送钱,三十元,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,当我欣然伸手去接的时候,老妈手快半路截走了佣金。担心我不服气,她还补充说,你花钱不少了,上学这么多年,头一次换来回头钱。说完,拉开抽屉,把佣金塞了进去,随手迅速关上,之后拉过一把凳子,用她微胖的身板挡住了抽屉,似乎怕它飞走。看我脸色不对,老爸和大姐都出来帮我。他们说不能这么干,你又不是剥削阶级,干嘛奴隶主做派。老妈嘴硬,脖子也硬,坚决不服气,还是重复原来那几句,好像我上学消费犯了什么罪似的。那天晚上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,她都不像我亲妈,像后妈,像奴隶主。我摊开双手,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以当时的眼光看,家有剥削阶级,是我的悲哀。一人之力,甚至三人之力,不能力挽,三十元钱稳坐抽屉一角,雷打不动,但我尚且倔强,不甘心做奴隶,还能以不再出山这一行动昭示一颗反抗之心。
那时候年轻,倔驴一样,说出去的话,泼出去的水,收不回。老妈手足无措,又无计可施。估计插秧的引申义并没有在她大脑形成任何意念,不懂后退的老妈不知道,闲在家中的我心中是多么地惬意。
直到有一天我走出村庄,又回来,插秧工依然在风起云扬的五月紧俏。我站在村庄的边沿,闻着一畦一畦的稻花香,看着满头白发身形伛偻的老妈,我不知道插秧工要留给我什么别样的记忆。